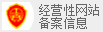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历经屈辱,终于站起来了。
在这百余年间,中国涌现了一大批爱国科研者,他们在战乱年代刻苦求学,以科学救国,以科技兴国,为中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魏曦就是其中一位。他虽不曾上阵杀敌,但他以优秀的科研技能助攻己方战斗,多次不顾个人安危奔赴前线,无惧枪林弹雨,无愧于“勇士”的称号。
爱国的热血青年
魏曦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湖南岳阳的一个小职员家庭。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他在中学时期就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与爱国青年一起组成演讲团,在家乡进行反帝爱国宣传。
在帝国主义笼罩的阴影下,时局动荡,战争频发。因自然灾害和战乱因素,湖南疫灾多发。1920年,岳阳城霍乱肆虐导致近万人死亡。眼看乡亲们贫病交加,国人被耻笑为“东亚病夫”,深受爱国教育的魏曦痛心疾首,当下决心学医。
坎坷的求学之路
抱着振兴中华医学的决心,魏曦开始坎坷的学医之路。
1921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预科班,两年后去南京金陵大学学习生物学,一年后又返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大学期间,他经常参加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参与反帝反军阀斗争,充当党组织的信使。1926年,北伐战争在长沙打响第一枪,魏曦因掩护叶挺部队的3名中共战士而遭到反动军阀的通缉,致使他被学校开除学籍,父母也被迫与其断绝关系。
大学三度肄业,被通缉,还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魏曦干脆加入北伐军,成为第四集团军警卫团三等军医正,随着部队拯救伤员。直至北伐在长沙取得胜利后,他到长沙广雅中学(今长沙市一中开福中学)任教了一年。
任教期间,魏曦不忘学医的初心,边教书边准备考学。1928年,他考上位于上海的中央大学医学院继续攻读医学,靠着手里的少量津贴紧张度日。期间,他还因患肺结核曾辍学过一段时间。
命途多舛并没有阻挡魏曦求学的脚步,他潜心学习并对时下新兴的微生物学产生浓厚兴趣。他在此领域潜心研究,于1933年凭借毕业论文《肺疽的细菌学》顺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留洋期间心系祖国
魏曦博士毕业后并没有按照最初的想法从医。随着越来越多致病菌被发现,微生物学科对医学的进步有重大意义。他想继续研究微生物学,叩开新学科的大门。于是他到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工作,五年里从助理研究员一步步成为研究员。
自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更加动荡不安,仅凭着一腔热血,在岌岌可危的国度闭门造车根本无法救国,只有走出去,学习更前沿的科研知识,才能为国做出更大贡献。1937年春,魏曦远渡重洋赴美深造,到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细菌学和免疫学,师从世界著名细菌学家和免疫学家秦瑟(Hans Zinsser )教授。
同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启全面侵华战争。日军违反国际公约,丧心病狂地在中国使用生化武器。魏曦得知此消息后,恨不能立马奔赴战争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于是他向导师申请回国。
导师劝他学习不要半途而废,与其赤手空拳回国,不如潜心研究,抓紧研制病毒的血清和疫苗,拯救更多同胞。他权衡利弊,化悲愤为动力,全身心投入科研,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无惧无畏的战地科研勇士
1939年,魏曦圆满完成学业从哈佛毕业回国。9月,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军在湘北对中国进行第一次大攻势,岳阳在日军的炮火下沦陷。这一次,魏曦又义无反顾加入湘北战场的战地医疗救护队。
装备落后,再加上药物匮乏,几乎没有能抗击毒气的生物制剂,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的生化攻击根本毫无反抗之力。正当魏曦一筹莫展之际,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中央防疫处处长的汤飞凡邀请他去中央防疫处当技正,为抗日军民生产急需的血清和疫苗。
魏曦随即前往昆明,协助重建中央防疫处和筹建中国第一个生物制品所。为搜集敌军投掷的毒菌,研制生物制品,他多次奔赴前线,在炮火连天处寻找样本。1944年,在汤飞凡的带领下,魏曦等人在昆明防疫处研制出中国第一批2万单位/瓶的青霉素,并陆续生产出质量达到欧美同类产品水平的伤寒疫苗、天花疫苗、白喉疫苗等生物制品支援前线。
他凭借着优秀的专业能力为反法西斯斗争作出巨大贡献。1945年,魏曦查明英美盟军“不明热”病的病因实为恙虫病。采用针对恙螨的防治措施后,“不明热”得到控制,大大保证了盟军战力。魏曦因此获得了哈佛大学考察团授予的“战时功绩荣誉勋章”(这枚荣誉勋章现保存在北京军事博物馆)。
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后,朝鲜战争又于1950年爆发,美军效仿日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危及刚诞生的新中国。魏曦毅然赴朝参加中国政府组织的美军细菌战争罪行调查团,并任检验队队长。他从美军投掷的细菌武器中分离出鼠疫和霍乱菌,揭露美军发动细菌战的罪行。因工作成绩突出,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
魏曦虽不曾上阵杀敌,但他以优秀的科研技能助攻己方战斗,多次不顾个人安危奔赴前线,无惧枪林弹雨,无愧于“勇士”的称号。
显著的科研贡献
魏曦除了为人正直、谦和,在学习上还非常刻苦,充满探索和创新精神。
他在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时,就开创了用鸡胚培养回归热螺旋体的方法;并且与汤飞凡教授合作,改进姬姆萨染色法,研究牛胸膜肺炎支原体,是我国最早研究支原体的学者之一。
在哈佛留学期间,他深入研究立克次体学,吸取前人失败经验,对实验方法进行仔细观察和详细分析,通过改进固体培养基的成分和改变直接培养立克次体的组织等办法,最终成功接种斑疹伤寒立克次体。这个课题在当时属于世界前沿技术,对量产疫苗有重大意义。因此,哈佛大学对魏曦进行嘉奖,授予他金钥匙。这项成果还给了同实验室工作的恩德斯(Enders John Franklin) 博士带来非常大的启示,他在84岁时曾给远在中国的魏曦写信表示,自己的成果是他们的共同大事。
在中国防疫处工作了8年后,魏曦成为上海医学院教授兼中央防疫处上海分处处长,期间他和助手用蚕蛹培养立克次体。1949年,他去大连解放区新建的大连医学院任一级教授、微生物学教研室主任兼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在大连工作期间,他所在团队首创研制出的干燥牛痘苗,解决了液体牛痘苗运输中失效的问题,由此获得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科研成果一等奖。
敢说敢做的科普者
魏曦是个极具科学精神的人,勇于质疑、谏言,以传播前沿科学知识为己任。
最值得称道的是,他早在上世纪50年代发现首例因抗生素导致菌群失调的病例时,就意识到滥用抗生素的严重性。同年就在学术论坛上尖锐地指出:“在光辉的抗生素时代来临之后, 还必须注意它给人类带来菌群失调的阴影。”他以渊博的学术知识预言了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才被广泛关注的问题。
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他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谏言。当时国内大兴水利、疯狂扩大水稻种植面积,魏曦直言必须同时注意媒介动物和病原微生物的散播,以免造成血吸虫病以及钩体病疫区的扩大。然而,当时他被认为是反对“三面红旗”而受到批判。在重重压力下,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率队亲赴现场考察,用事实证实了自己的预言。
除了致力于中国预防医学和生物制品的研究,魏曦还是积极的科普引路人。1981年,78岁高龄的魏老依然活跃于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会,并把“悉生生物学”等有关概念引入国内。对待科学,他与时俱进且勤于思考,否定了日文“无菌生物学”的译法并提出“悉生生物学”的概念,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赞同。他促成了中华预防医学会微生态学学会的成立和《中国微生态学杂志》的创刊,参与主编《正常菌群与健康》《微生态学》两部专著。
魏曦坚守在科研一线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1989年,魏曦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他丰富的人生经历见证了中国历史,他的爱国精神和科学精神将激励着后人。